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
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得清清爽爽。
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直到我入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
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
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
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中,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
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
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旨与基本的,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
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
入学,要交十元的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
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
新年到了,正赶上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投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
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像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是母亲的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昨夜还看见新月,今晨起来,却又是浓阴的天!空山万静,我生起一盆炭火,掩上斋门,在窗前桌上,供上腊梅一枝,名香一炷,清茶一碗,自己扶头默坐,细细地来忆念我的母亲。
母亲逝世,今天整整13年了,年年此日,我总是出外排遣,不敢任自己哀情的奔放。今天却要凭着冷与静,来细细地忆念我至爱的母亲。
13年以来,母亲的音容渐远渐淡,我是如同从最高峰上,缓步下山,但每一驻足回望,只觉得山势愈巍峨,山容愈静穆,我知道我离山愈远,而这座山峰,愈会无限度的增高的。
激荡的悲怀,渐归平静,十几年来涉世较深,阅人更众,我深深地觉得我她,不只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实在因为她是我平生所遇到的,最卓越的人格。
她一生多病,而身体上的疾病,并不曾影响她心灵的健康。她一生好静,而她常是她周围一切欢笑与热闹的发动者。她不曾进过私塾或学校,而她能欣赏旧文学,接受新思想,她一生没有过多余的财产,而她能急人之急,周老济贫。她在家是个娇生惯养的独女,而嫁后在三四十口的大家庭中,能敬上怜下,得每一个人的。
在家庭布置上,她喜欢整齐精美,而精美中并不显出骄奢。在家人衣着上,她喜欢素淡质朴,而质朴里并不显出寒酸。她对子女婢仆,从没有过疾言厉色,而一家人都翕然地她的言词。她一生在我们中间,真如父亲所说的,是清风入座,明月当头,这是何等有,能包容的伟大的人格呵!
十几年来,母亲的生活在我们的忆念之中。我们一家团聚,或是三三两两地在一起,常常有大家忽然沉默的一刹那,虽然大家都不说出什么,但我们彼此晓得,在这一刹那的沉默中,我们都在痛忆着母亲。
我们在玩到好山水时想起她,读到一本好书时想起她,听到一番好谈话时想起她,看到一个美好的人时,也想起她--假如母亲尚在,和我们一同欣赏,不知她要发怎样美妙的议论?要下怎样精确的?我们不但在快乐的时候想起她,在忧患的时候更想起她,我们爱惜她的身体,抗战以来的逃难,逃警报,我们都想假如母亲仍在,她脆弱的身躯,决受不了这样的奔波与惊恐,反因着她的早逝,而感谢。但我们也想到,假如母亲尚在,不知她要怎样热烈,怎样兴奋,要给我们以多大的鼓励与慰安--但这一切,现在都谈不到了。
在我一生中,母亲是最用来慰励我的一个人,十几年教师,主妇,母亲的生活中,我也就常用我的去慰励别人。而在我自己疲倦,烦躁,颓丧的时候,心灵上就会感到的迷惘与!我想:假如母亲尚在,纵使我不发一言,只要我能倚在她的身旁,伏在她的肩上,闭目宁神在她轻轻地摩抚中,我就能得到莫大的慰安与温暖,我就能再有勇气,再有去应付一切,但是:13年来这种,竟无法填满了,悲哀,失母的悲哀呵!
一朵梅花,无声地落在桌上。香尽,茶凉!炭火也烧成了灰,我只觉得心头起栗,站起来推窗外望,一片迷茫,原来雾更大了!
恕我不往下写吧,--有母亲的小朋友,愿你永远生活在母亲的恩慈中。没有母亲的小朋友,愿你母亲的美华永远生活在你的人格里!
我是一个最爱母亲的人,却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少的人。我六岁离开母亲,以后有两次短暂的会面,都是由于回家奔丧。最后一次是分离八年以后,又回家奔丧。这次奔的却是母亲的丧。回到老家,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连遗容都没能见上。从此,人天永隔,连回忆里母亲的面影都变得迷离模糊,连在梦中都见不到母亲的真面目了。
这样的梦,我生平不知已有多少次。直到耄耋之年,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对享受母亲的爱来说,我注定是一个的悲剧人物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关于母亲,我已经写了很多,这里不想再重复。我只想写一件我决不相信其而又热切希望其的小事。
在大学念书时,母亲突然去世。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赶回清平,送母亲入土。我回到家里,看到的只是一个黑棺材,母亲的面容再也看不到了。
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在里间的土炕上,一叔陪着我。中间隔一片枣树林的对门的宁大叔,径直走进屋内,绕过母亲的棺材,走到里屋炕前,把我叫醒,说他的老婆宁大婶撞客了--我们那里把鬼附人体叫做撞客--,撞的客就是我母亲。
我大吃一惊,一骨碌爬起来,跌跌撞撞,跟着宁大叔,穿过枣林,来到他家。宁大婶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嘴里却不停地说着话,不是她说话,而是我母亲。一见我(毋宁说是一听到我,因为她没有睁眼),就抓住我的手,说:儿啊!你让娘想得好苦呀!离家八年,也不回来看看我。你知道,娘心里是什么滋味呀!如此刺刺不休,说个不停。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懵懵懂懂,不知所措。
按理说,听到母亲的声音,我应当嚎陶大哭。然而,我没有,我似乎又过来。我在潜意识中,连声问着自己:这是可能的吗?这是真事吗?我心里酸甜苦辣,搅成了一锅酱。
我对母亲说:娘啊!你不该来找宁大婶呀!你不该麻烦宁大婶呀!我自己的声音传到我自己的耳朵里,一片,一片淡漠。然而,我又不能不这样,我的那一点科学起了支配的作用。母亲连声说:是啊!是啊!我要走了。于是宁大婶睁开了眼睛,木然、愕然坐在土炕上。我回到自己家里,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希望它是真的。倚闾望子,望了八年,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独子,对母亲来说不也是一种安慰吗?但这是多么渺茫,多么神奇的一种安慰呀!
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总会不时想起一条老狗来。在过去七十年的漫长的时间内,不管我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不管我是在亚洲、在欧洲、在非洲,一闭眼睛,就会不时有一条老狗的影子在我眼前晃动,背景是在一个破破烂烂篱笆门前,后面是绿苇丛生的大坑,透过苇丛的疏稀处,闪亮出一片水光。
无论用多么夸大的词句,也决不能说这一条老狗是逗人喜爱的。它只不过是一条最普普通通的狗,毛色棕红、灰暗,沾满了碎草和泥土,在乡村群狗当中,无论如何也显不出一点之处,既不凶猛,又不魁梧。然而,就是这样一条不起眼儿的狗却揪住了我的心,一揪就是七十年。
因此,话必须从七十年前说起。当时我还是一个不谙的毛头小伙子,正在大学读西洋文学系二年级。能够进入园,是我平生最满意的事情,日子过得十分惬意。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是在秋天,我忽然接到从济南家中打来的电报,只有四个字:“母病速归。”我仿佛是劈头挨了一棒,脑筋昏迷了半天。我立即买好了车票,登上开往济南的火车。
我当时的处境是,我住在济南叔父家中,这里就是我的家,而我母亲却住在清平官庄的老家里。整整十四年前,我六岁的那一年,也就是1917年,我离开了故乡,也就是离开了母亲,到济南叔父处去上学。
我上一辈共有十一位叔伯兄弟,而男孩却只有我一个。济南的叔父也只有一个女孩,于是在表面上我就成了一个宝贝蛋。然而真正从心眼里爱我的只有母亲一人,别人不过是把我看成能够传接代的工具而已。这一层道理一个六岁的孩子是无解的。可是离开母亲的痛苦我却是理解得又深又透的。
到了济南后第一夜,我生平第一次不在母亲怀抱里睡觉,而是孤身一个人躺在一张小床上,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我一直哭了半夜。这是怎么一回事呀!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了呢?“可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母亲当时的心情,我还不会去猜想。现在追忆起来,她一定会是肝肠寸断,痛哭决不止半夜。现在,这已成了一个之谜,永远也不会解开了。
从此我就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不能说,叔父和婶母不喜欢我,但是,我惟一被喜欢的资格就是,我是一个男孩。不是亲生的孩子同自己亲生的孩子感情必然有所不同,这是人之常情,用不着掩饰,更用不着美化。我在感情方面不是一个的人,一些细微末节,我体会极深。
常言道:没娘的孩子最痛苦。我虽有娘,却似无娘,这痛苦我感受得极深。我是多么想念我故乡里的娘呀!然而,天地间除了母亲一个人外有谁真能了解我的心情我的痛苦呢?因此,我半夜醒来一个人偷偷地在被窝里吞声饮泣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
在整整十四年中,我总共回过三次老家。第一次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为了奔大奶奶之丧而回家的。大奶奶并不是我的亲奶奶;但是从小就对我疼爱异常。如今她离开了我们,我必须回家,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一次我在家只住了几天,母亲异常高兴,自在意中。
第二次回家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原因是父亲卧病。叔父亲自请假回家,看自己共过患难的亲哥哥。这次在家住的时间也不长。我每天坐着牛车,带上一包点心,到离开我们村相当远的一个大地主兼中医的村里去请他,到我家来给父亲看病,看完再用牛车送他回去。是土,坑洼不平,牛车走在,颠颠簸簸,来回两趟,要用去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至于医疗效果如何呢?那只有天晓得了。反正父亲的病没有好,也没有变坏。一叔到济南来接我回家。
这是我第三次回家,同第一次一样,专为奔丧。在家里埋葬了父亲,又住了几天。现在家里只剩下了母亲和二妹两个人。家里失掉了男主人,一个妇家怎样过那种只有半亩地的穷日子,母亲的心情怎样,我只有十一二岁,当时是难以理解的。但是,我仍然必需离开她到济南去继续上学。在这样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但凡母亲还有不管是多么小的力量,她也决不会放我走的。可是她连一丝一毫的力量也没有。她一字不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能够取上。做了一辈子“季赵氏”。
到了今天,父亲一走,她怎样活下去呢?她能给我饭吃吗?不能的,决不能的。母亲心内的痛苦和忧愁,连我都感觉到了。最后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爱的孩子离开了自己,走了,走了。谁会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儿子呢?谁会知道,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呢?
回到济南以后,我由小学而初中,由初中而高中,由高中而到来上大学,在长达八年的过程中,我由一个浑浑沌沌的小孩子变成了一个青年人,知识增加了一些,对人生了解得也多了不少。对母亲当然仍然是不断想念的。但在暗中饮泣的次数少了,想的是一些切切实实的问题和办法。
我梦想,再过两年,我大学一毕业,由于出身一个名牌大学,抢一只饭碗是不成问题的。到了那时候,自己手头有了钱,我将首先把母亲迎至济南。她才四十来岁,今后享福的日子多着哩。
可是我这一个奇妙如意的美梦竟被一张“母病速归”的电报打了个。我坐在火车上,心惊肉跳,忐忑难安。哈姆莱特问的是to be or not to be,我问的是母亲是病了,还是走了?我没有法子求签占卜,可又偏想知道个究竟,于是我自己想出了一套占卜的办法。我闭上眼睛,如果一睁眼我能看到一根电线杆,那母亲就是病了;如果看不到,就是走了。
当时火车速度极慢,从到济南要走十四五个小时。就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我闭眼又睁眼反复了不知多少次。有时能看到电线杆,则心中一喜。有时又看不到,心中则一惧。到头来也没能得出一个肯定的结果。我到了济南。
到了家中,我才知道,母亲不是病了,而是走了。这消息对我真如五雷轰顶,我昏迷了半晌,躺在床上哭了一天,水米不曾沾牙。像大毒蛇直刺入我的心窝。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难道你就不能在任何一个暑假内抽出几天时间回家看一看母亲吗?
二妹在前几年也从家乡来到了济南,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单影只,而且又缺吃少喝,她日子是怎么过的呀!你的和哪里去了?你连想都不想一下吗?你还能算得上是一个人吗?我,找不到一点能原谅自己的地方。我一度曾想到,母亲于地下。但是,母亲还没有埋葬,不能立即实行。在极度痛苦中我胡乱诌了一幅挽联:
叔父婶母看着苗头不对,怕真出现什么问题,派马家二舅陪我还乡奔丧。到了家里,母亲已经成殓,棺材就停放在屋子中间。只隔一层薄薄的棺材板,我竟不能再见母亲一面,我与她竟是人天悬隔矣。我此时如万箭,痛忍,想一头撞死在母亲棺材上,被别人死力拽住,昏迷了半天,才醒转过来。
抬头看屋中的情况,真正是家徒四壁,除了几只破椅子和一只破箱子以外,什么都没有。在这样的中,母亲这八年的日子是怎样过的,不是一清二楚了吗?我又不禁悲从中来,痛哭了一场。
现在家中已经没了女主人,也就是说,没有了任何人。白天我到村内二大爷家里去吃饭,讨论母亲的安葬事宜。晚上则由二大爷亲自送我回家。那时村里不但没有电灯,连煤油灯也没有。家家都点豆油灯,用棉花条搓成灯捻,只不过是有点微弱的亮光而已。有人劝我,晚上就睡在二大爷家里,我执意不肯。让我再陪母亲住上几天吧。在茫茫百年中,我在母亲身边只住过六年多,现在仅仅剩下了几天,再不陪就真正抱恨终天了。于是二大爷就亲自提一个小灯笼送我回家。
此时,万籁俱寂,在一片中,只有天上的星星在眨眼,仿佛闪出一丝。全村没有一点亮光,没有一点声音。透过大坑里芦苇的疏隙闪出一点水光。走近破篱笆门时,门旁地上有一团黑东西,细看才知道是一条老狗,静静地卧在那里。狗们有没有思想,我说不准,但感情的确是有的。
这一条老狗几天来大概是陷入困惑中:天天喂我的女主人怎么忽然不见了?它白天到村里什么地方偷一点东西吃,立即回到家里来,静静地卧在篱芭门旁。见了我这个小伙子,它似乎感到我也是这家的主人,同女主人有点什么关系,因此见到了我并不咬我,有时候还摇摇尾巴,表示亲昵。那一天晚上我看到的就是这一条老狗。
我孤身一个人走进屋内,屋中停放着母亲的棺材。我躺在里面一间屋子里的大土炕上,炕上到处是跳蚤,它们勇猛地向我发动进攻。我本来就毫无睡意,跳蚤的干扰更加使我难以入睡了。我此时孤身一人陪伴着一具棺材。我是不是害怕呢?不的,一点也不。虽然是的棺材,但里面躺的人却是我的母亲。她永远爱她的儿子,是人,是鬼,都决不会改变的。
正在这时候,中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听声音是对门的宁大叔。在母亲生前,他帮助母亲种地,干一些重活,我对他真是感激不尽。他一进屋就高声说:“你娘叫你哩!”我大吃一惊:母亲怎么会叫我呢?原来宁大婶撞客了,撞着的正是我母亲。我赶快起身,走到宁家。在平时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此时我却是心慌意乱了。只宁大婶嘴里叫了一声:“喜子呀!娘想你啊!”
我虽然头脑,然而却泪流满面。娘的声音,我八年没有听到了。这一次如果是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那有多好啊!然而却是从宁大婶嘴里,但是听上去确实像母亲当年的声音。我信呢,还是不信呢?你不信能行吗?我胡里胡涂地如醉似痴地走了回来。在篱笆门口,地上黑黢黢的一团,是那一条忠诚的老狗。
我又躺在炕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两只眼睛望着,仿佛能感到自己的眼睛在发亮。我想了很多很多,八年来从来没有想到的事,现在全想到了。父亲死了以后,济南的经济资助几乎完全断绝,母亲就靠那半亩地维持生活,她能吃得饱吗?她一定是天天夜里躺在我现在躺的这一个土炕上想她的儿子,然而儿子却音信全无。她不识字,我写信也无用。
听说她曾对人说过:“如果我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这一点我为什么过去一点也没有想到过呢?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现在这两句话正应在我的身上,我亲自感受到了;然而晚了,晚了,逝去的时光不能再追回了!“长夜漫漫何时旦?”我却盼天赶快亮。然而,我立刻又想到,我只是一次度过这样痛苦的漫漫长夜,母亲却度过了将近三千次。这是多么的一段时间啊!
在长夜中,全村没有一点灯光,没有一点声音,仿佛凝结成为固体,只有一个人还瞪大了眼睛在玄想,想的是自己的儿子。伴随她的寂寥的只有一个动物,就是篱笆门外静卧的那一条老狗。想到这里,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再想下去了;如果再想下去的话,我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母亲的丧事处理完,又是我离开故乡的时候了。临离开那一座破房子时,我一眼就看到那一条老狗仍然忠诚地趴在篱笆门口。见了我,它似乎预感到我要离开了,它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在我腿上擦来擦去,对着我尾巴直摇。我一下子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我们的永别,我俯下身,抱住了它的头,亲了一口。我很想把它抱回济南。但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我只好一步三回首地离开了那里,眼泪向肚子里流。
到现在这一幕已经过去了七十年。我总是不时想到这一条老狗。女主人没了,少主人也离开了,它每天到村内找点东西吃,究竟能够找多久呢?我相信,它决不会离开那个篱笆门口的,它会永远趴在那里的,尽管脑袋里也会充满了疑问。它究竟趴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最终是饿死的。我相信,就是饿死,它也会死在那个破篱笆门口,后面是大坑里透过苇丛闪出来的水光。
我从来不信什么;但是,我现在宁愿信上一次。我已经九十岁了,来日苦短了。等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会在天上或者地下什么地方与母亲相会,趴在她脚下的仍然是这一条老狗。
母亲生前没有摄取坐像的照片,但这姿态清楚地摄入在我脑海中的底片上,不过没有晒出。现在就用笔墨代替显影液和定影液,把我母亲的坐像晒出来吧:
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开间的楼厅,右边是我的堂兄家,左边一间是我的堂叔家,中央是没有板壁隔开,只拿在左右的两排八仙椅子当作三份人家的界限。所以母亲坐的椅子,背后凌空。
若是沙发椅子,三面有柔软的厚壁,凌空无妨碍。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几根木条,其高只及人的肩膀。母亲坐着没处搁头,很不安稳。母亲又防椅子的脚摆在泥土上要霉烂,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衬在椅子脚下,因此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很不便利。
所谓西北角,就是左边最里面的一只椅子,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退堂里就是灶间。母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顾,可以看见灶头。风从里面吹出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堂前隔着三四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母亲坐在椅子里向外面望,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听到沸反盈天的市井声,很不清静。但我的母亲一身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这样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静的一只八仙椅子上,眼睛发出严肃的,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冲要。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
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六人,薄田数亩和染坊店一间而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
我从学堂里放假回家,又照例西北角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有时这四班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架不住,于是她用眼睛的严肃的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了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当时的我看惯了这种光景,以为母亲是天生成坐在这只椅子上的,而且天生成有四班人向她缠绕不清的。
我十七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诫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她给我准备学费,她给我置备行李,她给我制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她给我做一个小线板,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
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
我廿二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不克依居母亲膝下,唯假期归省。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
我三十岁时,弃职归家,读书著述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
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她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我从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三十三岁,
不,直到现在。陶渊明诗云:“昔闻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现在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觉得十分恐惧。这每次给我以深刻的和有力的勉励。
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更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她一边捶打野菜一边哭泣才符合常理,但她不是哭泣而是歌唱,这一细节,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它所包含的意义。
我母亲没读过书,不认识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真是难以尽述。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我在母亲生前,一直想跟她谈谈这个问题,但每次我都感到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
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办。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
“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有时候家里没有了青菜,母亲会牵着我的手,穿过屋前的一片芒花地,到番薯田里去采番薯叶,有时候到溪畔野地去摘鸟莘菜或芋头的嫩茎。有一次母亲和我穿过芒花地的时候,我发现她和新开的芒花一般高。芒花雪一样的白,母亲的发丝墨一般的黑,真常美。那时感觉到能让母亲牵着手,真是天下最幸福的事儿。
还经常上演的一幕是,父亲到外面喝酒彻夜未归,如果是夏日的夜晚,母亲就会搬着藤椅坐在晒谷场说故事给我们听,讲虎姑婆,或者孙悟空,讲到孩子们都睁不开眼而倒在地上睡着。
有一回,她说故事说到一半,突然叫起来:“呀!真美。”我们回过头去,原来是我们家的狗互相追逐着跑进前面那一片芒花地,栖在芒花里无数的萤火虫霍然飞起,满天星星点点,衬着在月光下波浪一样摇曳的芒花,真是美极了。我再回头,看到那时才三十岁的母亲,脸上流露出欣悦之情,在星空下,我深深觉得母亲是那么美丽。
今世,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也没用,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有无穷无尽的笑声,一遍一遍又一遍,回荡了整整三十年,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本文来源于ipf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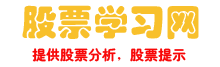



 删除。
删除。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