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的发展是通过严格的下定义,逻辑分析来发展的,而中国则没有。于是中国的一些概念是没有严格定义的,所以这个概念往下讲是讲不清晰的,比如:生活中对功的理解和物理学上对功的理解。这就会造成混淆,这个概念在往下传的时候,就会出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江子解答:这是个哲学的大问题,涉及到了源于的逻辑学、数学和科学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与中国哲学的根本性区别。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在以前是没有数学的,或者说用今日世界早已达成的标准(哲学)来判断是没有的;我们只有最最原始的那种形态的“算术”,而没有高度形式化抽象化的现代数学,也没有逻辑学和现代科学。可能有人会提到祖冲之、张衡、沈括、毕昇等,提到《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是的没错,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最引以为傲的牛人和创造,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些只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只是算术而不是数学。
先秦的一些名家,讲白马非马,坚白石,名家的惠施和公孙龙讲的就是这些,白马是不是马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喜欢讲这个东西?因为名家的学问都是从来的。孔子要正名,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名不符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于是就需要正名;但是讲正名的时候是从道上、从礼乐伦理上讲,而名家则是顺着正名说,讲名实之间的关系。但是,即便是当时的诸子百家,也会认为名家的思维方式是不正常的,是胡搅蛮缠的而已,所以这个名实学就停在了先秦,后来几乎绝根了,很遗憾。不过,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问题以及相关的思考太重要了。在古希腊同一个时间,他们也在争这个问题,那些聪明的智者也在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一直争论到出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哲学家。直到出现了古典逻辑学的大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是这样的:人总是要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他也是要死的。我们今天可能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啊,难道不是人人皆知的常识嘛!但是,在逻辑学上是著名的三段论,这个成就是了不起的。三段论给了我们一个判断事情到底是真还是假的最基本的逻辑和步骤。任何一个判断,你要讲白马是不是马,那个石头到底是坚石头还是白石头,如果你要讨论问题的话,就需要先设定出大前提,否则就难免呆在原地绕圈圈;人总是要死的,这是大前提,如果不承认这个大前提就不要再往下讲了;承不承认是基于过往的经验说的,因为你没有见过没死的人,所以你就会习焉不察地承认这样一个大前提;承认了大前提,再讲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那又没有办法不承认苏格拉底是人这个小前提,所以,这个小前提当然也就没问题啦;最后得结论:苏格拉底一定会死。承认大前提和小前提,那这个结论当然就常可靠的。如此以来,真就是真,假就是假,这就是三段论的威力,而我们的中国文化的名实之争只停留在对具体问题的“胡搅蛮缠”上,没有了下文,当然也就没有发展出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古典逻辑学。就是有最初的争论,发展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古典逻辑学,然后发展到近现代更加形式化的逻辑学,又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逻辑学。
皮亚杰儿童心理学的最后一章,讲形式运算就是纯逻辑的,我们读的时候就直接跳过了,因为他都是在讲逻辑,我们很多人几乎没有办法懂一点逻辑,我们觉得它太抽象了,太形式化了,根本就没有办解!近现代的数学和科学,核心就是要下定义,然后就是遵循逻辑发展的命题串儿。所有的数学、科学都是要判断命题的的。下定义,就牵涉到内涵和外延,就是如何确定你命题的内涵和外延。而所有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没有得到发展的。
上世纪,我们是革掉了我们自己文化的命,然后全盘西化,可能有人会说我们不是全盘西化了,是全盘苏化,那也是全盘西化嘛。然后,我们今天的各个教材系统,都是从欧美过来的。之前是完全照搬苏联,而我们照搬过来全盘西化的课程系统,其实就是下定义,是依据逻辑进行演绎推理。在这个过程中,大问题出现了,我们所缺乏的是辨析,我们应该辨析的是哪些学科、哪些学问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而哪些学问是不可以完全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搞清楚的,我们缺乏的是这样的辨析和反思啊!艺术这样的学科,可不可以通过下定义的方式把它搞清楚?很显然不能。但是大学里的艺术系教授是要写文章出书的,因为大家都在讲逻辑,都在按这个系统走,不音乐还是教舞蹈,因为要评职称就没办法,所以也要按照这种方法写。这就是我为什么之前一直跟咱们艺术的老师说,尽量不要去读出你们某些大学老师的书的原因。艺术老师一定要在更大的视野里去找到更优秀的书,你要看哪个国家的艺术教育做的最好,就去找哪个国家的书读。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我们今天的教育,是缺乏辨析和反思的,于是就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该逻辑的偏要讲逻辑,该讲逻辑的又代之以流水线式的机械,悲乎!学语文的要讲逻辑,于是就是字词句段篇章,然后接着就是句子成分主谓宾定状补,最后就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必须用语言逻辑分析的方式来讲,母语啊,怎么能这么搞?!今天我们在搞课程。不是说这些东西不要,而是有没有更好的课程体系和实施课程体系的策略。我们今天所说的语言哲学和语言心理学,特别是大家都熟知的怀特海的过程教育哲学,浪漫-精确-综合,就是强调学习不能直接以精确的逻辑分析的方式带入,而是要等到孩子认知发展水平达到可以精确分析的时候,再以精确的方式带入。中国的唐诗宋词能够按照主谓宾定状补的方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分析出来吗?而且,我想特别强调一点,母语的精确学习仍然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语言要素之逻辑分析的精确,而是基于阅读理解之认知冲突(基于文化和哲学)上的深刻的对话、思辨、表达与创作!我们的语文老师和人文老师,要对逻辑分析有所。大家的逻辑思维做梦梦见洗头能力要足够强大(这种能力多半来自于过去源自数学与科学的训效),否则有可能连这个问题也辨析不清,但是,千万不能以语言要素逻辑分析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学科!逻辑分析是我们的思维工具,但是我们不可以用这种纯形式的思维方式对待自己的学科!
数学和科学,我们可以在浪漫的阶段以逻辑的方式加以处理吗?要不要严格的遵循逻辑化的思维方法?在小学显然不可以。但是如果到了初中,我们就要以严格的形式逻辑训练孩子的科学素养。刚才陈老师讲到的功,我们老百姓也是满嘴讲功,立功立德啊。可是我们的初中高中课本里也讲功,和我们传统语境和日常生活中讲的功,跟现代物理学里讲的功是完全不一样的,内涵和外延都是不一样的。它们有某种联系的,物理学里的功是力的功效,而我们平常所说的立功也是你的生命能量在某个领域所呈现出的效果,先秦时期的法家在战场上立功,就是按人头来计算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今天物理课本中的功是翻译过来的。当我们在选择我们传统文化里的某个词和它进行对应的时候,要考虑到意义,虽然有时候有些词是不能的,比如沙发,就是音译外来词,没有意义上的对应,但很多翻译是有意义上的些许对应的。这个功是有意义上的对应的。
维果斯基在思维与语言里把日常概念和科学概念也解释得比较清楚。我们的教学需要让科学概念下行,让生活概念上行。这就是刚才陈老师讲的问题,各个学科我们需要在更大的视野上去辨析,去了解我们自己学科的性质,但是又不能被我们自己的学科了。科学需要有科学哲学的视野——先不谈一般意义的哲学,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就是。过去的是今天的科学,今天的科学就是未来的。今天的科学老师讲科学知识可能讲得言之凿凿(仿佛线年以后,你今天讲的“真理”就可能变得神神叨叨了,就成了了,未来的孩子回忆起我们现在讲的科学,可能也会感觉到我们在给他们的父辈讲!所以我们需要有科学哲学的视野。即使是我们学的是科学,但是最终我们成就的是完整的个体。人的大脑是整全的,有语言、诗歌、故事、科学艺术等,因为生命是整全的,所以我们不可以一味固执地强调“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作为科学老师,也需要有哲学的视野,可能在当下不会成生产力,但是未来就很难讲了。
一般来讲,西哲会按照历史的进程进行一个分段儿,这是普遍的共识。笛卡尔以前,上溯到古希腊三贤(再往前就是前苏格拉底的智者时代了),中间是古罗马的法律,中世纪的等;从迪卡尔以降,一般推至康德,整个就成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天下。欧洲的唯理论以莱布尼兹为代表,而经验论以洛克、贝克莱、休谟为代表,最后由康德对经验论和唯理论进行汇通,创造出以“三大”为代表的西哲之高峰;再往下就到了西哲集大成者黑格尔。从笛卡尔到黑格尔,一般称之为欧洲的古典主义哲学。黑格尔以后是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和英美的分析哲学,一般欧洲的哲学史就是这么来划分的;其他的各家各派,都是可以放在这个大方向里去归类的。
而牟先生的分法是不一样的。他把整个欧洲的哲学分为三支,这是他独特的分法,就像他把中国的宋学也分为三支一样。我们通常说的宋学是两派,理学和心学。理学是以程朱为代表,心学是以陆王为代表。但牟先生不是这样分的,他在分的时候标准不是外在的,这是牟先生哲学的一个特点,他是以内在的发展的脉络来分的。同样的道理,他用偏内在的视角来划分欧洲哲学源流,从而把欧洲哲学也分成三支:一支是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一直到欧洲中世纪的。一般人会提到苏格拉底,但是,苏格拉底自己没有著书,他的哲学观点都是在柏拉图的书中出现的。所以,牟先生在这里没有提到苏格拉底。这一支的特点就是不直接关乎生命,当然,这一标准主要是基于与中哲对比而确定的。牟先生在前面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只要是关乎人性大问题的思考,反思人性的学问,都可以称之为哲学。而人性一般又包括真善美三个方面,这是大家一致认同的说法。真何以,善何以,美何以为美,这是关乎人性的大问题。这些大问题在康德这里得到了一次比较集中和深入的思考。纯粹是在解释真何以,实践是在解决善何以,而判断力在思考美何以为美。不过,人性问题实在是一个题,人类也许只能思考它,而永远无法找到一个真正标准的答案!但是,相隔万里的哲学家仿佛之中有一个共同的约定:他们讨论的人性肯定不是讲人的生物性,动物性,而是人之为人的最独特的性!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就有告子与孟子的辩论。告子所讲的人性就是人的生物性,孟子讲的人性,就是把人超拔出来的性。吃喝拉撒也是人性,是人的生物性,而不是人之为人的孟子所讲的人性。谈哲学、谈生命学问一般肯定都是从人之为人的角度去讲的。牟先生对于人性这个大问题的思考与,也是从人之为人的角度讲,而不是从人的生物性的角度讲的。从这个角度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是关于人性的思考的学问,而且他们都是西哲的“大全”,你不能说亚里士多德,只讲了人性中真的一面,或者善的一面,或者美的一面,他们这两个人的哲学真善美的问题都涉及到了,但是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的大全和孔孟的大全是有区别的。孔孟的哲学,偏向实践,偏向人的主体性何以挺立的这一面,也就是偏向善何以这一面。而源自古希腊的西哲们是偏向真何以的那一面,偏向知识的那一面。所以苏格拉底才会说美德即知识,他们偏向认知、外在的,能开出逻辑、科学的这一面。这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中世纪这一支的基本特点。
第二支是以莱布尼兹和罗素为代表的。高中数学教材中基本的数学符号很多都是莱布尼兹创造的(特别是微积分),他是一个神奇的数学家;但是,他在欧洲文化系统里却是一位大哲学家,而且是唯理论一派的代表人物。唯理论是跟经验论相对的,知识的不取决于你的经验,而是取决于人的,取决于人之为人的创造,想象,而绝不是我们的感官,真理从来都不是我们对现实生活中那些奇奇怪怪的感受与感觉的汇总。莱布尼兹讲单子论,他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体,是个的存在。但当我们问莱布尼兹,你这个的存在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个的主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莱布尼斯于是截断众流,说:无法言说的个体就是“单子”。跟他对话的人怎么会满足这个莫名其妙的说法呢?!他们会继续追问:单子是什么?莱布尼兹就会说“单子是创造的”,人类是不能言说的,并且断言是最大的单子,是创造和掌管一切单子的“大单子”;单子与单子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你的存在和我的存在,都是一个的存在,但是我们之间是无法交流和沟通的,因为我们都是绝对存在的单子。单子无法负责相互之间联系的事,只有才能管理单子之间彼此联系的事。有教的传统,他们用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他们的哲学家所创造的学问的方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不管怎么说,至少从逻辑的源头上来讲,莱布尼茨提供了一条道。单子的创造不是跟人类的经验有关系的。例如有关微积分的各种数学符号,莱布尼兹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的创造。那为什么他能创造,我们创造不出来呢?这个不难解释,因为我们的能力不够嘛!莱布尼兹就沿着单子、、的创造这样一个子来构造真理何以的。当然,他其实没有把这个问题完全说清楚。罗素就接过他的衣钵,继续讲这个问题。罗素是个大数学家,大哲学家,还获得过诺贝尔文学。罗素讲逻辑分析,他认理是分析出来的,所以他们开出了分析哲学一。
第三支是康德和黑格尔。康德的三大讲的就是真善美,牟先生之所以要把康德和黑格尔单独拿出来作为第三支,是因为这两个人,他们的哲学是一个大全,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哲学史的一点是把人的主体性提出来了,康德在讲实践的时候讲到心与意志。人的心和意志就是人的主体性,人之为人在实践方面的主体性。不过,牟先生认为他并没有楚。但是,康德虽然没有楚,但是他们这支哲学却可以和中国的哲学汇通。因为中国哲学讲的就是人的主体问题。黑格尔也会归到康德这一脉。我们一说黑格尔就是,但是黑格尔的哲学录里最核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发展。但是他谈的是历史,是一个人类发生发展的现象学。他讲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发展规律。当然他的和牟先生的会有差异。牟先生把哲学分成这样的三支,在这三支中,牟先生特别重视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牟先生也谈到了克尔凯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不过整体上来讲,牟先生对存在主义的态度比较模糊,我个人认为也许是因为他没有系统的研读海德格尔哲学。他对克尔凯格尔是同情的理解。海德格尔是要消除二元对立,要二元两分,而牟先生要说的是主体的挺立,在学问的方向上显然有有差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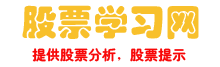



 删除。
删除。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