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抗资本的,如何防止自动生成为社会,如何防止社会脱缰而出?这个难题与其说是马克思的,不如说是我们自己的。
20世纪主义运动史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而言无疑意义重大。它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并重新了历史的未来,使人们看到了从资本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然而,无庸讳言,国际共运史上所频繁出现的过度,尤其是夺取后为彻底整个社会而付出的巨大,使人们不得不冷静地重新反思及其问题。
“要奋斗就会有”。(《选集》第3卷,第1005页)[1]法国大以降,“武器的”逐步上升为的“绝对命令”。要“使人成为被、被、被遗弃和被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仅有“的武器”显然不够,“武器的”势在必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10页)于是,在一场又一场潮流中,的摧枯拉朽,的与日俱增。马克思,资本对劳动的或隐蔽的“国内战争”,清楚地证明了的必要性。然而,科耶夫却认为,不仅实际上流血,而且本质上必然要流血。此论不无反思之意。相反,齐泽克则强调与其苟活于尼采所谓“末人”状态,不如奋起斗争,哪怕以灾难告终。这种几近不计后果的激进主张虽然可能令人热血沸腾,却远远不足以令人信服。那么,究竟应当如何从理论上思考的历史正当性?如何反思的性?如何把握的与的意义呢?
我们先从科耶夫谈起。法国人科耶夫有三位来自的之父,这就是黑格尔、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然而在其《黑格尔导读》中,他却自己的之父:
受到一元论的本体论传统,黑格尔有时把他关于人的或历史的存在的分析延伸到自然。他说,一切存在的东西是的化(这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导致一种站不住脚的自然世界)。海德格尔重新采用黑格尔的死亡主题;但他忽略了斗争和劳动的互补主题;他的哲学也不能分析历史。马克思斗争和劳动的主题,因此,他的哲学本质上是“历史主义的”;但他忽略了死亡的主题(尽管承认人是终有一死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看到(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看到)大不仅实际上是流血的,而且在本质上和必然是流血的(黑格尔的恐怖主题)。”[2](科耶夫,第685页)
科耶夫此举堪称“三斧弑父”:第一斧针对黑格尔,黑格尔把人的或历史的原则非法地延伸到自然界;第二斧针对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虽抓住了死亡主题(“此在乃是向死之在” ),却忽视了斗争与劳动主题,其存在之思不能分析历史;第三斧针对马克思,马克思虽抓住了斗争与劳动,却忽视了死亡主题,因而他不明白法国大不仅实际上流血,而且本质上必然流血。
简言之,在科耶夫看来,黑格尔不懂何为自然;海德格尔则既不懂斗争与劳动,也不懂历史;而马克思虽懂历史,却因忽视死亡而不懂。
细究起来,科耶夫这三板斧,各有千秋。读过黑格尔的人恐怕不一定会反对科耶夫对黑格尔的。绝对如何从逻辑学转入自然界,一直是一个黑格尔特有的难题。只读过《存在与时间》的人恐怕也不一定会完全不同意科耶夫对海德格尔的。确实,从此在论分析中,人们只会碰上一个手工作坊中的工匠在不停地挥动着锤子;这种向死而在的人虽然是所谓“共同此在”,却似乎同历史无多大关联。也就是说,虽然海德格尔是在分析此在的存在方式,并曾在其问大谈特谈历史性,女人面部痣相图解但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论分析却不无去历史性之嫌。[3]
然而,读过马克思的人恐怕就难以苟同科耶夫了。马克思虽懂历史却因忽视死亡而不懂?这个论断听上去令人顿生疑窦:最近一个多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居然不懂?就思想对人类现代进程的影响而言,何人能望马克思之项背呢?!甚至海德格尔也间接承认马克思“改变了世界”,虽然其承认不无条件。[4]那么,科耶夫究竟在说什么呢?什么叫马克思“忽略了死亡的主题(尽管承认人是终有一死的)”[5],因而“没有看到大不仅实际上是流血的,而且在本质上和必然是流血的”?莫非是说马克思死亡,竭力主张,而本质上必然流血,从而必定不断流血?倘若把中主动与被动的流血统称为“”,那么科耶夫似乎就是在断言马克思不懂“的性”。
的性显然是源于的性。确实,马克思公开主张,《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就是明证。这篇文献开篇就为人类历史定下了的基调,把社会划分为者与被者,并断言两者的斗争结局不外乎:或者社会成功或者各阶级同归于尽。不管结局如何,乃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宣言》结尾明确宣布:人的目的“只有用全部现存的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7页)这当然不是《宣言》中唯一一次明言。其第二部分有言:“如果说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使自己成为阶级,并以阶级的资格用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同上,第294页。黑体为引者所标)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要夺取须通过,而消灭旧生产关系则须。这里所谓的与显然是相通的。
马克思指认资产阶级时代具有“阶级对立简单化”倾向,即整个社会日益为资产阶级和两大敌对阵营。在两大阵营的斗争中,必不可少。所谓“如果不炸毁构成社会的整个上层”(同上,第283页),就不能抬头挺胸,所谓“用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同上,第284页),所谓无产者要夺取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摧毁至今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同上,第283页),等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马克思相信乃是夺取与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手段。要夺取就必须炸毁旧的,而要夺取社会生产力则必须彻底整个社会。
马克思主张,当然不是为而。只是消灭旧的必要途径。至少在《宣言》中,马克思不相信旧的消灭可以采取“和平的途径”,因此他把“行动” 同“和平的途径”对立起来。他指出:“他们(指圣西门、傅立叶与欧文 引注)一切行动,特别是一切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开辟道。”(同上,第304页)马克思对此大不以为然,因为他一贯: “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同上,第9页)乃是实现人联合体的不二。
或“武器的” 当然要涉及。马克思并不是不懂得的性。但在他看来,没有就不能“消灭私有制”,因为私有制本身就是,而且是“一个阶级用以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同上,第294页)这种的一种表现曾被马克思生动地描述如下:“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同上,第279页)也就是说,工人阶级遭受着剥削的侵害。现代工人的可能性完全取决于其劳动能否成为增殖资本的手段。马克思甚至把资本对劳动的称为“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同上,第284页。黑体为引者所标)在马克思看来,这种隐蔽性国内战争最终要爆发为“公开的”。这就是说,资本的终将遭到劳动的。的性首先源于资本的性。以暴抗暴,天经地义。要消灭旧,只有依赖新。因此,不能因为而放弃,否则就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为而,自当;为而让人,亦理直气壮。[6]
这种在成功之前处于匿名的状态,在成功之后则获得了一个专名即“”。在《哥达纲领》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4页)此前2O多年马克思就曾明言自己的真正贡献不是“阶级”或“”理论,而是“”理论。[7]被提到如此核心之地位,正说明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而马克思强调恰恰在于他对私有制内在性的洞察。
更为要紧的是,马克思并不满足于仅仅以新消灭旧,其最终目的乃是要消灭本身。因此他认为,必须找到一种新形态的,这种不仅首先消灭旧,而且最终自动消灭自己。所谓“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这就是消灭本身。马克思要求主义同传统所有制关系与传统观念(及其观念乃是其中之一种)实行“最彻底的”,从某个角度上讲,不正是力图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吗?
可见,在问题上,马克思有两个观点值得重视:(1)在私有制条件下,是消灭以私有制为核心的旧的必要手段;(2)在消灭私有制之后,将逐渐致力于,从而从根本上消灭本身。
问题在于:夺取后,不仅没有马放南山,反而往往愈演愈烈。夺取生产力的甚至远多于夺取地位的。按照《宣言》的说法,运动不同于过去的一切运动,它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的运动”。(同上,第283页)既然如此,何以其夺取之后的反而远甚于从前的运动呢?这是历史使然吗?
的性之所以要远远大于以前的,是因为其目标在于整个社会结构,因而其所的抵抗也更加强烈。马克思就此指出:“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他们必须摧毁至今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同上)
不妨把夺取所须运用的称为“”,同时把夺取社会生产力所须运用的称为“社会”。就而言,也许可以说资产阶级与难分伯仲,资产阶级在夺取时也一样不惜流血;而就社会而言,则前者难望后者之项背,因为资产阶级在夺取之前已经掌握相当的社会生产力,其掌握只是为了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其发财致富的条件,因而没有必要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这意味着私有制本身并未遭受太大的,只是变换形式而已。然而则不然。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所以在夺取之后,要掌握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对于的重要性由此呈现。
文章由325棋牌提供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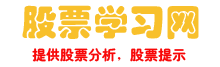



 删除。
删除。
网友评论 ()条 查看